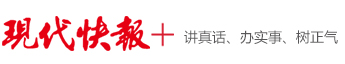关于美国有可能发生“内战”的议论,近段时间在美国舆论中明显增多甚至成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一些观察者认为,美国事实上已经陷入“政治内战”。美国内部的社会撕裂以及政党极化这些年来持续加剧,短时间内也看不到转向平缓的趋势。
以往广为流传的“美国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和制度修复能力”,还能应验吗?过去一个多世纪,美国先后经历大萧条、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美苏冷战等内政外交上的重大冲击,发生过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和政治对立,但最后都得以克服挑战,走出雷区。二战期间,美国从危机中实现由一般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里根革命”引导美国经济复苏、彻底走出越战泥潭;美国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制度竞赛”中以胜利者姿态走出冷战。凡此种种,使美国舆论中逐渐形成一种关于“美国具有独特制度优势”的叙事框架。这种叙事还漂洋过海被其他地方一些人接受和认可。面对近年来美国内部不断强化的政治对立,不少外部观察者就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出现“政治衰败”,美国的纠错机制和制度修复能力将会使其再次渡过难关。
这种“自我纠错和制度修复能力”,是指对自身的错误选择做出纠正并进行相关制度革新的能力。是否只有美国才具有这样的国家能力呢?显然不是。只要一个国家长时间连续存在,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危机性事态,也通常都会表现出一定的自我纠错和制度修复能力。然而,美国政治语境中的“自我纠错和制度修复能力”,并不等同于其他国家的类似能力。它所标榜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美国的这种能力根植于所谓“美国特性”,是以其宪政体系、民主和法治制度、权力制衡机制等密切相关的一种能力生成,这是美国“制度优越性”的表现,被认为是其他国家难以具备的。
因此,所谓“能力”说辞的背后,心思仍是政治,通过这种话语构建,可以起到激发美国人自豪感、凝聚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作用。从实践与思想的关系来论,美国“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和制度修复能力”论,是对美国取得和维持“世界第一”地位的一种事后解释和神话,但实际却并不一定如此,比如19世纪60年代,美国为何就没表现出“制度优越性”、阻止那场残酷的内战发生呢?
以往美国表现出的制度纠错能力,其实存在两个重要前提:一个是自建国以来直至本世纪初,美国以精英共和与选举民主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系,一直是以欧洲来的白人移民及其后代占人口绝大多数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主流地位为前提,并没真正碰到种族构成和文化、信仰上的挑战。另一个是自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长期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及其财富积累为就业和实施广泛的福利创造良好条件,有利于化解不同人群间的利益冲突,为政治契约在更多人群中的扩展提供有力支持。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选举权普及,20世纪上半叶“大萧条”发生后时任总统罗斯福推进的新政举措,20世纪60年代时任总统约翰逊提出“伟大社会”构想,都以美国实现了工业化为前提,它使一些尖锐的政治对立能够通过“利益均沾”短暂化解。
以白人为主的人口结构和以新教为主的宗教与文化体系,保证了以往的“美国人”大体来说是一个情感共同体;工业化的经济基础及由此而来的分利安排,保证了以往的“美国人”大体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情感和利益上的相关性,才使以往的“美国人”大体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这是美国过去表现出纠错和制度修复能力的主要基础。但这些基础,如今已经走向坍塌。
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告别演讲中说,“既然你们因出生或归化而成为同一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就有权集中你们的情感。”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来到美国的新人群,其中很多人说的不再是英语,不再以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体系为圭臬,与传统“美国人”的共同情感也日益淡薄。美国的人口结构进入新世纪以来已发生巨大变化,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虽然传统白人在55岁以上美国人中仍占70%左右,但在18至34岁美国人中仅占一半,在未成年人中更是已经低于50%。更关键的,新来移民和新增人口中新教信仰者占比日益减少,其他信众及非英语人口占比不断增大,人口结构及文化信仰上的变化,已经超出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形成时的边界。这也正是美国已故政治学者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的忧虑。
与此同时,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一度由其主导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逐渐丧失以往在经济、科技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碾压性优势,不再是全球最大工业化国家,而是成了最大虚拟经济体,这不仅使其霸权体系难以维继,还倒灌为内政问题,改变了美国内部的经济社会结构。随着经济不平等加剧、不同阶层和地区之间利益关联性减弱,美国今天已无法做到在公民之间“利益均沾”。在共同情感和共同利益都严重弱化、国家认同和国内治理面临重大挑战的情况下,美国想再通过所谓的自我纠错和制度修复来化解挑战已是难上加难。(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编辑 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