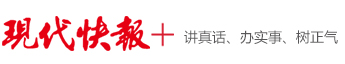现代快报讯(记者 张垚仟/文 牛华新/摄)十一月的第三周,诗人欧阳江河来到南京,分别在先锋书店、东南大学与镜见博物馆展开了三场对谈与分享。天气寒冷,欧粉们热情依旧。他们簇拥着欧阳江河,听他谈论对于诗歌写作最新的思考,也向他询问关于诗歌阅读与写作的疑惑以及对当下中国诗坛的看法。
因为他是欧阳江河,他被国际诗歌界称为“最好的中国诗人”。这些年他的简介上陆续添加了策展人、书法家等头衔,但即使是在未写诗的十年中,他也从未停止对诗歌写作的思考。从《玻璃工厂》到《凤凰》,欧阳江河每一阶段写作的代表作品都对诗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在对诗歌写作理论的思考上,他也一直保持着先锋的姿态。

欧阳江河的诗歌写作,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一直带有几分“冒犯”的意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欧阳江河与同时代的一批诗人共同完成了对特定年代诗歌写作中普遍存在的集体无意识、大而不及物的词语的转变,对当时习惯了教科书式语言的人们是一种极大的“冒犯”。欧阳江河回忆起自己有一次在四川大学进行演讲,有两个女生“当场昏倒”,因为她们受不了他那种巫术化、原创性和民间性的语言表达。这种对于旧有的话语体系的冲击可见一斑。
这个时期的“冒犯”不仅体现对外部话语体系的扭转,也蕴藏在欧阳江河写作的内部——离开中国古典文学对他的影响。他创作最早的代表性作品《悬棺》的初衷,就是为了对自己古代中国文学的情结做一个了断,真正进入现代诗歌写作。
1997年,欧阳江河结束四年的异国生活回到国内。面对消费主义对写作的影响、写作与五花八门的现实之间诡异的关系,他以诗人的眼光打量和质疑这个世界,也以诗人的身份沉默了。他将诗歌放在与生命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因此他不愿意“装写”:“装写可以不停地写,越写越划算,因为你在走下坡路嘛,连油门都不用加。但我坚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我欧阳江河身上。诗歌写作在我的内心深处,有过非常严肃的掂量。一条命啊,我凭什么一定要写诗呢?我可以干很多其他的事儿,但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写诗?那肯定我的生命在里面。”
十年未写诗之后,欧阳江河携长诗回归诗坛。在他看来,长诗写作不仅是抵抗消费主义、碎片化阅读的方式,也是在冒犯“正在中国大地上蔓延的抒情写作、自我感觉良好的审美的写作。”欧阳江河认为,当代诗歌的写作陷入了“优美”的圈套,对于仿写性的依赖已经过了头,丧失了原创性。因此,他试图用诗歌的语言来处理被人们认为是诗歌范围外的东西——新闻的、调侃的、冒犯的,这是他这个阶段写作的内在“骨力”。欧阳江河直言不需要批评家的理解与读者的喜爱,因为他很清楚写作最终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
欧阳江河打算将“冒犯”的阶段至少延长到七十五到八十岁,剩下的岁月他会反过头去写讨好读者们和批评家们的写作,“但是在那件事之前,对不起,在我变甜之前,在我变亮之前,让我再黑暗一点、再苦一点、再酸一点、再难吃一点。”
实际上,对于欧阳江河当下的写作,许多文学评论家毫不吝啬他们的赞赏。德国汉学家顾彬评价《泰姬陵之泪》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全世界写得最好的一首诗。而另一位德国重要的批评家认为欧阳江河的诗歌呈现了世界背后的“供电系统”。
“灯泡打开,散发出来的光;水龙头拧开,流出来的水,这些都是我们读到的文本,但是它的后面,得有一个供电系统、供水体系。”如果说生活现场与精神标高的关系是灯泡发出的光、水龙头里流出的水与供电系统、供水系统的关系,那么欧阳江河的诗歌呈现的正是世界后面暗布的那个供电系统、供水系统。欧阳江河认为,“散发出来的光”与“流水来的水”当然也是一种写作,但文学作品的创造,光有生活现场还不够,还必须要有精神标高的支撑,富有精神和思想的文学作品。
在欧阳江河看来,现在很多人的文本甚至连发光的“灯泡”都算不上,使用的语言充其量是一种“鼠标语言”,“‘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什么语言啊,那种手机文化的、消费文化的、碎片文化的这种语言。”语言的碎片化和语言的鼠标化,反应出来的是正是人的知识体系的萎缩,人与世界联系的断裂。
欧阳江河提倡中国古典诗歌“虎豹”一般的语言,“谢公文章如虎豹,至今斑斑在儿孙”,但在欧阳江河看来,古人虎斑纹理一般的语言、堂堂皇皇的文章已经逐渐丧失。在长诗《黄山谷的豹》中,他描绘了虎豹追逐自己,而自己供养虎豹的情景,用来表明自己对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的推崇。“我愿意用我来喂养它,但在喂养之前,让我们先跑一跑,我来成为逃者。这样我完成与中国豹子一样完美语言融为一身的过程:我在逃避这个命运,但我又最终成为这个命运。”
年轻时,谈起中国古典诗词,欧阳江河大概不会用“推崇”这样的词语,但不可否认,中国古典诗词对欧阳江河以及他们那一代诗人有着深刻的影响,写作形式上的泾渭分明无法割断文化基因与文化身份的内在血脉。
“像我这样的当代诗人,据我所知,像于坚、翟永明,尤其是西川,包括张枣、柏桦,我们对古诗用力极深,我们都有古学底子,我可以背数百首古诗,甚至根本不用背,它自动就来了。在我们最先锋、最革命的时候,最决绝的时候,最繁荣的时候,它还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起作用。只是我们越老,越用一种让自己都有点儿羞愧的、欣赏的语气在谈这些,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是用革命的语气,用跟它决裂的这种语气在谈它。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回归、欣赏、萦绕,萦绕其中的这样一种东西在谈到它。”
谈及最近大热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欧阳江河表示叶嘉莹式的写作无法代表这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也没有原诗写作的挑战,不可能有人的律诗写得比杜甫还好。“所谓‘百凶成就一词人’,诗词写悲哀、写个人的身世和时代精神的对应。这些主题和这种写法已经变成一个惯性,没有独创性。它不是‘无中生有’了,是‘有中生有’。你可能会写得更好,更有特色,但是你加入到的是那个‘有中之有’,而且在那个‘加入’里面你怎么写得过杜甫?写不过的。杜甫写律诗,形式上的最高典范,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他已经达到了神一样的高度。”
但欧阳江河非常欣赏叶嘉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只有成熟而古老的文明才具有的“弱德之美”,“当我在说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的时候,汉语和中文是一个大语言的时候,我更多地在说它是一种老语言,但它又经过了今天的更新,它是一个‘弱’语言。它的强大在于它承认这个弱的存在,这个柔弱,这个水一样柔软的这种眼泪,这是一个反词,没有任何对应物。它的对应物绝不是‘强大’,强大不是它对手。强大马上就被转化为‘弱’的一部分,马上被转化为‘弱’的一个低音的、一个持续的铺垫。就像划一根火柴在黑暗之中立即就消失了,变成黑暗的,但是它闪了一下,就这个火柴晃了一下,让你看清了自己的面孔还有他人的存在。”
对话
诗歌语言如何与其他话语进行对话?
现代快报读品:如何理解您所说的诗歌语言与其他话语间的对话?
欧阳江河:科学话语与政治话语对话构成了核武器,当科学话语、物理话语、数学话语与资本对话的时候构成了商业中的电脑之类的,不同的话语之间对话产生了另外的东西,但是诗歌语言能与他们对话吗?我指的是语种上的对话,比如说小说可以处理科学话语,产生了科幻。但是诗歌呢?我想干的是这个,所以我写的是《宿墨与量子男孩》,我构成了“量子男孩”这个形象,我认为是我的一个贡献。而中国的批评家们、写作者们、读者们可不一定能够很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但这没关系,我处理了诗歌话语,就像政治话语和科学话语的对话,医学话语和疾病的对话,资本话语和科学的对话,它们产生了新的品种、变种和形象,提取出来,器物提取出来,改变了文明。最后呈现的是不同的文明。那么诗歌话语来处理这些时候,它能在文明意义上呈现什么新的可能性。我写这个诗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我举个例子啊,我是想在这种意义上,文明的这个意义上,长时段的文明的意义上,而不是在短时段的、瞬间的自我抒情和塑造和灵感的意义上写诗,我退出来了,我退出了自我,我泯灭掉自我了。我在一个无我的地方,回过头来,我在三百年以后的另一个星球上回头看地球,这一瞬间,我把我的生命输入到现在这个欧阳江河的肉身上。但是我已经带了三百年以后的另一个星球的密码了。我回到这时,我来看,我想在长时段的意义上理解,用诗歌来理解和处理,也可能我的理解是错的,但没关系,我想处理这个,哪怕诗歌本来,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错的产物,诗歌不是正确的,诗歌不寻求正确意义上的真理,它不像科学,科学也允许试错啊。
现代快报读品:最近在阅读什么书?
欧阳江河:今年读了很多历史书和很多经典性质的书,原来破破碎碎地读过,现在重读。比如说冯象翻译的《圣经》,之前我读的都是传教士翻译的版本,还有全本的《古兰经》。我在读《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同时,对读《从吉本到奥登》,这本书是研究了十九世纪到现在所有重要的历史研究的著作。还有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因为我前年年底去了埃及之后对阿拉伯历史特别感兴趣,这本书影响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康德对这本书也很感兴趣。然后我在对读英国学者写的《伊本·赫勒敦》。这种对读非常有意思。
欧阳江河
1956年出生于四川泸州。著名诗人,诗学、音乐及文化批评家,知识分子写作倡导者。 欧阳江河被国际诗歌界誉为“最好的中国诗人”,其代表作有长诗《悬棺》《玻璃工厂》《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傍晚穿过广场》《最后的幻象》《椅中人的倾听与交谈》《咖啡馆》《雪》等。
- 江苏
- 2021-09-12 21:22:19
- 江苏
- 2021-09-12 20:59:30
- 江苏
- 2021-09-12 20:10:07
- 江苏
- 2021-09-12 19:48:57
- 江苏
- 2021-09-12 18:5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