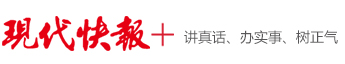费孝通先生在他那本著名的《乡土中国》里写道:“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自从进入农业社会以来,人类的衣食大致都要向土地索取,因此对土地产生了浓厚的依恋。我们的祖先将为自己提供生存所需的一方天地称为“家园”,到异地谋生叫“背井离乡”,身故之后也要“落叶归根”——前者凄凉,后者悲壮。
然而,人类的繁衍在理论上是无尽的,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却是有限的。当一片土地上的人口超过了其承载的最大限度,总有一些人要像带芒的种子离开麦穗一样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另一片适合生根发芽的土地。他们通过刀耕火种、披荆斩棘,开辟新的家园,然后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如此周而复始。人类的文明,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传承和散布开来。
步入工业时代后,驱动群体迁徙的力量不再只是对生存资源的寻求,而是对更好生活的向往。但我们的集体记忆中始终残存着安土重迁的DNA,我们的社会文化依然维系着与“家园”之间的精神脐带。当科技使人类的生存空间得以从横向转为纵向延伸,人类聚集之地的发展模式由二维空间的扩张变成了三维空间的膨胀,由此产生了现代城市。“安家”的涵义,也从拥有一片土地,变成与他人共享投射在同一土地上的生存空间——住房。在大部分人的观念里,到了新的环境后,迟早得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在万家灯火组成的星座图中占据一个固定的坐标,才算是在新的土地上“生了根”,拥有了自己的“家园”。
出生于城镇的我,大部分时候与土地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隔阂”——水泥、碎石、瓷砖、地板……因此,我虽不至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掰苞谷、打果子、掏鸟蛋、摸泥鳅等许多农村孩子都有的经历,于我是全然陌生的。不过,当他们享受大自然给予的无穷乐趣的时候,我却在几面墙围起来的方寸之间,醉心于另一片完全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天地。
我的房间里有一个旧式玻璃书柜,里面堆着大人们看完后随手搁置的各种“闲书”。对儿时的我而言,书中没有颜如玉也没有黄金屋,却有着鲜衣怒马、快意恩仇的江湖,有着天马行空、奇幻诡谲的世界。从学校到我家大概要步行十分钟,每当那座灰色的楼房离我越来越近,我的心情就会越来越好,因为我知道,在这一天所剩无几的时间里,那叫做“家”的空间将为我挡住外界的纷乱嘈杂,让我开始一段精神的旅程——那是我少时最快乐的时光之一。书里的人和事,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模糊,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书中的大千世界无数次地召唤我:到更远的地方去!
终于,在一个秋天,我拖着人生中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行李箱,坐上了从家乡到北京的绿皮火车。那个曾经给过我很多快乐的“家园”,在我离开后的某个时候,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轰轰烈烈的城镇改造与扩建中。与此同时,我也开始了在大城市跌跌撞撞的“奋斗”历程。
在人们的印象中,“奋斗”是个积极向上的词汇,它往往与“青春”“理想”这类意象联系在一起。仿佛提到“奋斗”,就是一个或一群热血青年追逐理想的青春故事。说来惭愧,我的“奋斗”经历,更多的是“挣扎”,是“试错”。除了隐约中有个世界在指引我前行之外,没有任何人告诉过去的我,那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模样,通往它的路又在什么地方。当我做完了试题、考上了大学之后,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对未来是迷茫的。
临近毕业,同学们都在寻找能落户的工作——这意味着在这个城市获得正式身份,以及这种身份带来的踏实感。我也随波逐流,按照上一辈规划的“最佳人生路线”迈出了第一步,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庸常,却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对远方的向往和对未知的恐惧这两股力量,时不时地撕扯着我。直到有一天,我决心离开那种安稳到几乎凝固的生活,重新去探寻远方。
一晃数年过去了,我没有找到书中鲜衣怒马、快意恩仇的世界,却像徐志摩说的那样,行过了许多地方的桥,看过了许多次数的云。我也目睹或听闻了他人形形色色的故事:北漂在北京周边买了房,每天上下班来回五个小时;互联网大厂员工辞去了高薪工作,到东南亚开起了民宿;在国外工作多年的知名企业高管回国做起了慈善事业;基层警察通过司法考试当上了律师……当然,更多的还是在按部就班、稳扎稳打中创造价值的故事。
如果从功利的标准来看,这些故事的底色有“奋斗”的,有“反卷”的;有“向上”的,有“向下”的;有“安居”的,有“放逐”的。但它们的主人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挣脱“当下”,奔赴“远方”,重寻“自我”。而在这样的倾听中,在与他者的联结中,我重新认识了真实的世界,发现了它的参差和层次、有趣和无常,也开始试着通过文字抵达更广阔的天地和更隐秘的角落。
我还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无论是租房还是买房,很少有人能同一个地方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要搬几次家,有时候是为了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有时候是为了更短的通勤距离,有时候是为了让孩子就读更好的学校,有时候是为了让年迈的父母上医院更方便……这让我不禁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形态早已分崩离析,任何年龄段的人们都可能因生活的需要而随时迁徙,那么,我们能够称之为“家园”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我想,如果只把“家园”定义为“住房”,未免过于狭隘。家园,应该是有形的空间和无形的信仰之间的结合。在农业时代,家园是养育人的一方水土,是远方游子的魂之所依;在工业时代,家园有了更多的功能和意义:它可以是人生出发的起点,也可以是实现自我价值的终点,还可以是完成某个阶段性任务的驿站。它既是让人为之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目标,又具有催人扬帆远航、乘风破浪的力量。
无论身处什么形态的社会,从一个家园抵达另一个家园的过程,就叫做奋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走错方向,可能会跌得鼻青脸肿、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只要不安于现状的小火苗还在胸膛跳动,我们总会像带芒的种子一样,风一来,就能飘到很远的地方。
奋斗的本质,是对远方世界召唤的回应,是跌倒后站起来继续前行的勇毅。只有通过一次次试错,我们才能校正自我的定位,实现人格的丰满,最终抵达精神的家园。
撰文/胡文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