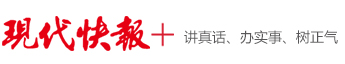现代快报讯(记者 陈曦)张定浩,一个喜欢诗歌、喜欢文学、喜欢批评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的名字。
他的诗歌《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最早在豆瓣受到豆友的喜爱和推荐,后经由北大民谣歌手程璧谱曲发布,为年轻人传唱,后来出版了同名诗集。而在更早的时候,他以初生牛犊的懵懂、敏锐和直率,把刀锋对准当代文坛业已功成名就的大佬——余华、苏童、格非、阎连科、马原等人,直击他们近年新作中的软肋与“命门”,获颁《南方人物周刊》“2019青年力量”。
“人们对一个人所产生的第一印象,不可避免地总会一直陪伴他。”因为批评当代名作家而成名的张定浩,写作的大部分重心,其实是那些过去时代的诗与人。他写过两本关于中国古典诗和现代诗的小书,《既见君子》和《取瑟而歌》,还写过一本解读先秦儒家经典的《孟子读法》。在他看来,写这些文章的过程,就是一次次去尝试接近那些伟大的心灵,是一次次主动而积极的自由教育。
近日,张定浩的两部代表作增订重版。《批评的准备及其他》是他2015年出版的首部文论集《批评的准备》的全新修订版。作者抽换掉原书三分之一篇幅,借此重新整理自己十余年来的文论写作,以表达对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认知。文章虽大多围绕当年出版的某部具体作品展开,但最终讲述的,是从这些具体作品中所感受到的普遍性问题。
另外一部谈论西方现代作家的文论集《爱欲与哀矜》的增订本,时隔六年,最终增加四万余字。以作者之见,爱欲不只是激情,也意味着失控,更是复杂的心智生活;哀矜则代表道德与责任。这两者都常让人难以承受,却是大多数旨在书写人类生活的出色小说家的选择。而作者本人长久以来的写作,有很大一部分也与此有关,都可以统摄在这个主题之下。
就自己的阅读、批评和写作,张定浩接受了现代快报记者专访。
源自不满的表达与解剖,在今天更有必要性

现代快报:书名为《批评的准备》。在你看来,从事文学批评需要做哪些准备?或者说成为批评家的要素有哪些?
张定浩:这个“准备”的用词,是在向罗兰·巴特《小说的准备》一书暗暗致敬。巴特说他一直想写小说,但始终只是处于准备阶段,这既是他的诚恳,却也不妨碍他写出一本关于小说的精彩著作。我用“准备”两个字想表达的是,这本书里的很多文章还不能算是地道的文学批评,因为在严格意义上,“批评”这个词,始终都是针对优异的作品而言,或者说,批评本就是对优异的辨识、召唤、理解乃至欲求。
成为批评家,和成为其他写作者一样,最重要的要素,可能就是诚。孟子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即如其所是,天地万物本来就是诚的,而唯有人,因为懂得谎言的艺术,所以只能无限度地去接近诚。
现代快报:文集中批评文坛大佬的那几篇文章,都涉及文学如何处理现实的问题。像纪录片一样去展示现实,在小说中简单粗暴地植入社会新闻,或是向壁虚构一种悖离真实生活的现实,都是你批评的。你认为文学应该如何处理现实?
张定浩:现实不是一个一眼可见的、对每个人都呈现同样面目的蛋糕。我眼中之现实未必是你眼中之现实。小说家能做的,不是去迎合他人眼中所看到的现实,同样也不是仅仅表达自己所看到的现实,而是要能够将自己化成各种各样的人,体会各种各样的现实,让这些不同的现实在自己的小说世界中相互映射。
现代快报:这批文章给你带来什么影响了吗?会不会因此得罪人?
张定浩:我只是“非常学术性”地去批评几个作家的作品,我相信读到的人自然能够体会我并没有什么恶意,所以也谈不上得罪人吧。我写文学批评文章的时候不会想着要产生什么影响或会不会得罪人,我会考虑的只是自己这些判断是否准确。
现代快报:成名对你意味着什么?
张定浩:可能意味着你知道有一些陌生人也在读你的作品。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影响,名声是别人给你的,别人也可以随时剥夺掉,和你自己没什么关系。
现代快报:现在写批评文章会有更多人际上的牵绊吗?
张定浩:不是因为人际的牵绊,如果你看我朋友圈就会发现我时不时还会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个人。我只是觉得自己要说的话大致就那些,多说都是重复。
现代快报:始终不愿意去写表扬稿式的评论文章。你觉得现在需要怎样的文学批评?
张定浩:我为什么要愿意去写这样表扬稿式的评论文章呢?写作对我来讲是自得其乐且不必扭曲自我的一件事。好的写作者都是文体创造者,并且拥有一种关于道德的精湛技艺,有力量通过他的作品,转变我们对何谓可能和何谓重要的看法,并为我们找到这个世界值得兴奋和希望的理由。糟糕的写作者则与此相反。
于是,对我而言,好的文学写作也随之成为一种好的、隐秘的批评,反之,文学批评首先也必须令自身成为一种认真而有力的写作,唯有如此,其所表达的一切才有意义,才值得珍重。
在此基础之上,对于普通的文学批评写作者,个人以为应该首先尽力做到的,唯有诚实而已,诚实地面对写作的困难,诚实地表达自己的判断。这判断进而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针对优异的辨识和欲求,二是源自不满的表达与解剖,后者虽然在美学上是无益的,但在今天的文学环境下,却似乎意外地具有某种伦理上的必要性。
好的作家、学者都是能够身兼多种身份

现代快报:《爱欲与哀矜》充满了诗性的表达,很多读者喜欢节选、摘录里面的“金句”,比如,“爱旋即意味着失控,而怜悯意味着责任。这两者,都是人类所不堪忍受的”“你要读的下一本书,或你要遇到的下一个人,会改变你的生命”……你觉得这本书的走红,是否与这些情感金句有关呢?
张定浩:不是因为它谈论了谁,而是因为它是怎么谈论的。“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这是古人对《古诗十九首》的评价,也是我自己写作的一个自我要求。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文学批评写作者也是一个道德作家,而在道德关怀的问题上,不存在什么金句,只有是否准确地击中你和影响到你。
现代快报:《既见君子》谈古代诗人,《孟子读法》解读儒家经典。一个现当代文学专业出身的人为何去研习古典?这些“业余写作”有没有遭过“专业人士”的质疑呢?
张定浩:好像目前为止,只遭遇过“业余人士”的质疑,因为如果真的是专业人士,他们会知道我写的是很专业的。现代的学科专业分工,本身就是非常滑稽的事,过去好的作家、学者都是能够身兼多种身份。具体到现当代文学专业和古典专业,它们其实本来就是一体的。我们历数一下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著名作家,比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俞平伯、朱自清等等,他们对古典都是非常精通的。古典是任何一个现当代作家和学者的基础。
具体到我的写作,我在写《孟子读法》的时候,几乎所有先前比较重要的孟子注疏我都读过,然后每一条都会在各家解读之间反复比较,这个阅读和比较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专业学习的过程。事实上,一个人成年之后的教育主要是依靠自我教育,这种自我教育是无止境的,从学校毕业只是这种自我教育的起点而已。
现代快报:诗集《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出版后,作为诗人的张定浩成立了。有一种现象是,批评家成名之后重新捡起诗人或小说家的身份,出版自己的小说或诗集,你对此怎么看?
张定浩:以前毛姆说过,每个人都有可能写出一部小说,但职业作家重要的是能一直写下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什么时机出版了小说或诗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一直出版下去。
现代快报:能说说你的阅读偏好吗?
张定浩:我喜欢比较好看一点的理论书,未必是文学理论。比如我就很喜欢查尔斯·罗森谈音乐的书,几乎每一本我都会买,他作为钢琴演奏家和音乐理论家,可以对于音乐作品做极细密扎实和完全出自内行的文本分析,同时又有非常开阔和博学的眼光,并且文笔也非常之好。最近看到年轻的中国钢琴演奏家张昊辰新出的《演奏之外》,非常惊艳,我没想到他有那么好的文史哲阅读功底,大概是我看到的中国音乐人写出来的最好的古典乐论。还有比如特里·伊格尔顿,我最近看他几本写于近年的著作,比如《论牺牲》《论幽默》《论文化》,那个理论材料爬梳和消化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同时又能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和拓展能力,并不仅仅是在罗列材料。这种书是在企图和读者对话,作为读者,你已经掌握的相关知识越多,这个对话就会对你越有收获,就像和一个比你杰出的人对话一样。
另外,如果说到文学书,我相对比较喜欢密度大一点的文学书。有些小说看起来很厚,但作者实际能够讲出来的有意思的东西并不多,那么就很浪费时间。比如托宾的小说,虽然也充满意识流的分析,但在他笔下的那个拥有意识的主人公是非常精彩的。这个也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样,很多人聊天可能聊一两个小时就原形毕露,就那么点东西翻来覆去,但有些人就可能会吸引你一直和他聊下去,因为一直有新的收获。
很多空间是靠自己的勇敢去争取出来的
现代快报:在你走上文学批评道路之前,曾经在安徽淮南火电厂做过五年的电工,后来到复旦读研,毕业后你曾辗转于出版社、民营出版机构和媒体,经历过短暂的彷徨期,那为何当初放弃电厂的工作呢?电工生涯对你的文学批评有什么潜在的影响吗?
张定浩:可能还是喜欢写作吧,也对种种不确定的生活有一种好奇。年轻的时候,都会喜欢不确定,喜欢尽可能踏上更多的道路。但到了一定年纪,会觉得时光有限,会希望在一条道路上尽可能走远一点。
其实不能叫电工,准确地说是电力工程师。工科比较讲究逻辑,具体到控制系统的设计和维护,则讲究信号的传递与反馈。这几点可能对我的写作有一点影响,我写文章会比较有逻辑性,同时我也会设想一个挑剔的读者如何反驳我,然后暗中和他展开辩论与说服的工作。
现代快报:现在年轻人似乎比较焦虑,渴望一步到位,过上一种确定的生活,不太愿意去“试错”。对于这种焦虑,你有何阅读上的建议?
张定浩:可能是外部大环境的种种不确定吧。我觉得不管什么情况下,年轻人多看看中西古典著作都是有益的,想一想柏拉图和孔子都生活在乱世,就会少一点抱怨。古希腊哲学家讲“认识你自己”,斯多葛派更强调一个人对于痛苦的感知、理解和消化的能力;中国儒家讲“反身而诚”,所有的事情先归返到自己身上,找自己的原因,不怨天,不尤人,诚恳地面对。此外,中西古典伦理学都强调“勇敢”这种美德,因为如果没有“勇敢”,很多其他的美德都会沦为空谈。
最近正好有一本《塞缪尔·约翰生传》,非常厚,但我觉得非常适合年轻人看,约翰生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读书和写作,克服自身的疾病和抑郁症,也克服出身环境和时代的局限,一生不懈奋斗,最终成为一个杰出的人。而在这个过程中,约翰生本人和这本新传记的作者都意识到,勇敢是这一切成功的基石。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里,很多空间都是依靠自己的勇敢去争取出来的。

△诗人、批评家张定浩 受访者供图
张定浩
诗人、评论家,《上海文化》副主编。1976年生于安徽,现居上海。著有文集《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诗》《孟子读法》《无形之物》,诗集《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等。
(编辑 周冬梅)
- 南京
- 2022-08-14 09:28:55
- 南京
- 2022-08-14 09:26:47
- 南京
- 2022-08-13 21:58:36
- 南京
- 2022-08-13 21:5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