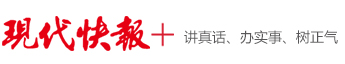文学作品是作家端给读者的晚宴,或惊艳,或家常,或不忍下咽,食客各有定论。至于每一道菜是如何做成,食材选择、刀功深浅、火候几分,则是作家秘而不宣的绝技。

△ 《钟山》杂志主编贾梦玮
作为资深文学编辑,《钟山》杂志主编贾梦玮,却执意邀请作家打开他们隐秘的后厨。这是一场历时 20 年之久的幻境旅行,读者得以进入朱苏进、王安忆、叶兆言、张炜、莫言、苏童、余华、贾平凹、毕飞宇、刘恒、韩少功等中国当代文坛名家的后厨,壁垒拆除,贴身体察。
《钟山》杂志的《河汉观星》与《将心比心》两个评论专栏,是这趟后厨之旅的摆渡者。二十年来,专栏文章先后结集为《河汉观星:十作家论》(2004 年)、《当代文学六国论》(2009 年)、《作家读作家》(2022 年)三种单行本出版,在最新出版的《作家读作家》后记中,贾梦玮谈及自己在这趟旅程之中的忐忑:" 真诚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最高境界,但受制于外在和内在的局限,真诚何其难也。读人读心难,说出来就是解密,解密就有风险 "。
在文学的王国里,导游贾梦玮悉心维护着渡船的稳当,把作家、评论家、读者递送到那个最相宜的观景平台。
帮作家找到他的 " 敌人 "
读品:《河汉观星》系列是怎么诞生的?
贾梦玮:《河汉观星》是一个专门的作家论的栏目,设置是在 2000 年前后,是出于对作家、对文学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和认识。当时的作家论太少了,思潮研究、作品研究很多,但是作家论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在文学的大的框架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也讲到,它是基础学科,所有基础学科的特点就是付出多、收效慢。一个作家论的研究者、批评家,他首先要把作家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读完,才能做这个作家论,工作量非常大。好多作家是通过我们《河汉观星》这个栏目,才有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家论。所以作家也是特别认可的,他不一定认可批评家的意见,但是对这样一个栏目,对批评家付出的劳动,作家是非常感动、非常理解的。之后,我们编了一本书叫《十作家论》,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
读品:《当代文学六国论》里对作家的评论非常尖锐,这个系列又是因何而起?
贾梦玮:做了综合的作家论以后,我就想,我们中国人以说别人的成就为主,然后说一点不足,我觉得这样做可能犹有不足。记得有一年我们好多主编在一起开会,我说,文坛批评的风气太单调了,能不能做一个 " 创作局限论 ",单挑作家的不足和问题来说,原来我们看到作家的正面,现在要看他的侧面,甚至要看他的反面。然后好多人在议论,说这个好。我说,你们谁做?然后大家都不说话了。我说好,既然你们都不做,只有我做了。
读品:涉及到的六位作家有王安忆、余华、张炜、莫言、张承志、贾平凹,为什么选他们?
贾梦玮:他们是当今中国文文坛最好的十多位作家之六,是非常值得做的大块头。当初选这六位作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再选六位批评家问题就来了。谁来做 " 创作局限论 "?因为我们文坛的老好人风气,所以批评家是不太愿意做的,吃力不讨好。当然有很多人打了马虎眼,包括说我最近特别忙,这个事情你看找年轻人做或者找其他人做,他自己就躲了。那么,最后这六位批评家当时都是青年批评家。我心里是很感动的,他们是支持我的,但是说得大一点,也是为了汉语文学的发展。我当时在后记、前言里面也说到,我们需要这些文学的好心人,因为作家他可能是没有敌人的,敌人如果一定要有,肯定是他自己。当局者迷,他自己不一定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问题。而且我们中国作家的问题可能都是基础病,是流行病,是传染病,比如说浮躁的毛病。那么从精神架构上来讲,精神资源上来讲,精神局限上来讲,我们的这几代作家可能也有很共通的地方,所以这六篇成书以后叫《当代文学六国论》。六个国家当然是比附古代的 " 六国 ",但是因为是精神创造,跟国家的幅员、国家的兼并是不一样的,每个作家都是个体的,打败自己的可能就是他自己。
读品:那么尖锐的批评,发表之后作家有什么反馈吗?
贾梦玮:我的感觉是,没有影响我跟作家们的关系,没有影响《钟山》跟他们的关系。刚发表的时候,他们可能心理上有点不舒服,因为说得那么尖锐,有时候甚至是 " 尖刻 ",可能一下子是接受不了的,但是时间长了发现,有人专门花那么多时间来找他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仗义、道义。
这其中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比如说洪治纲写的《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这个文章发表以后,《文学报》马上就转载了,我本家贾平凹老师也没有在意,转载就转载了。当期报纸刊载的时候,全国作协正好开代表大会,《文学报》人手一份,大家全看到了,纷纷猜测这后面有什么阴谋吗。这个时候我们都扛住了。过了一段时间,这篇文章居然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再后来发现,其实没有什么阴谋。所以我后来也跟我们的年轻编辑讲,我说文学这一行,真诚是第一位的。在出于公心、出于真诚的前提之下,做一点挑刺找毛病的事情,对文学的发展一定是有利的。而且在出发点是好的前提之下,我们的方式方法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的。
说出另一个作家的秘密
读品:《作家读作家》是通过一位作家的眼睛看另一位作家,这个系列的缘起是什么?
贾梦玮:有了 " 创作局限论 " 之后,有的作家提出了意见,说都是你们批评家在说话,甚至有人夸张地说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就想到,如果让作家来评说作家,让作家来评说他们的同行,可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我们每个人从生下来就在阅读,小宝宝出世以后睁开眼睛,他其实就在阅读,通过眼睛、通过耳朵在阅读这个世界。我们作家阅读世界的眼光,可能有人说心多一窍也好,打开天眼也好,他有他的阅读通道和方式,有他体验的表达的方式。作家谈另外一个作家,因为他们都是文学创作者,不仅知道里面的甘苦,也知道里面的种种的辛酸秘密,由他们来现身说法,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读品:这本书里收了十三位作家写另外十三位作家,当初是如何确定人选的?
贾梦玮:当时我们重新设立一个栏目叫《将心比心》。都是我们编辑提前选好的名单,选好的作家,就是结对子,背后都有编辑的推手在。包括毕飞宇写莫言,朱文颖写苏童、范小青,鲁敏写的叶弥,所有的这些,我觉得都是很真诚的。大家常说有一颗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我觉得都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个里面也会出现问题,说出秘密本身就是犯忌的。一个作家把读者带到另外一个作家的后厨,其实也是冒风险的。所以这个栏目开过两年以后,也遇到了寻找合适作者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说,我来写王安忆,他们说的都不对,我说的才对,我最了解我最理解。我说那太好了。但是过了几天,他打了个电话给我,说还是不能写。他还是有顾忌了,说假话他是不愿意的,完全说真话,他怕引起别人的误解,引起同行的误解,引起朋友的误解。
读品:从书里面看,是刘庆邦写了王安忆。
贾梦玮:他写得挺好,他们两个的私交也好。作家之间的私交,更多的是精神意义上的,如果没有精神意义上的互通,这种关系是不牢靠的。作家的有些心里话自己会作为秘密,但是另外一个人帮你说出来的时候,这种感动是无以言表的。所以作家之间的精神沟通,如果把它表达出来,对两个精神个体之间的这种友谊,甚至是一种促进一种鼓励。
读品:《作家读作家》收录的文章,写作时间距现在已有 10 多年了。重读这些文章是什么感觉?
贾梦玮:跟我当初的感觉基本是相同的,因为是作家谈作家,不是谈作品,一些基本的面还是一样的。这些年这里面的作家基本上都有新作了,旧的文章里新作就没有谈到,把新作再结合进去, 10 年的时间对一个作家来讲可能也有发展,甚至可能还有倒退,这个都是可能的。如果有机会,其实我们还想把这个栏目再重新建立起来,再写一下。也许我们大家能把我们真诚的东西焕发出来,能把这个栏目继续下去,我觉得对于作家对于文学可能都是有利的。
读品:就作家写作家而言,比如当年鲁敏写叶弥,毕飞宇写莫言,十年之后请他们再写一下,肯定又不太一样。
贾梦玮:《河汉观星》的栏目,我们还在继续,但是 " 局限论 " 跟 " 将心比心 " 要把它重新捡起来,还是需要一些条件,因为包括我这样的编辑,其实锐气也在衰减,我也不复当年的自己了,所以它需要很多条件。
作家的 " 技穷 " 与 " 道穷 "
读品:作为一位资深的文学编辑,如果给中国当代作家挑毛病,您会说什么?
贾梦玮:我们中国一些作家现在不是技穷,而是道穷,对社会人生、对文学的认识,有一些扭曲的地方。迎合了一些东西,其实也是对自我的一些委屈。有些作家的扭曲委屈可能是暂时的,但是有些作家可能再也回不来。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才华是必须的,但是在一个作家身上,技和道有时候是不能完全分开的。他对社会人生的敏感,他的文学的情怀,他的文学的理解,文学的体察和表现,在一些文学创造者身上,可能是某种先天的,但是我有一次开玩笑打比方,我说,才华对一个作家来讲,就像男人和女人的帅和美貌一样,你有这个非常好,但是你不能时时知道自己很美,甚至知道自己很美以后还去搔首弄姿,去把它做了其他的用途,那可能才华就被浪费了。我看到过很多有才华的作家,到了中年以后写的文章,你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所以才华是必备的,但是光有才华可能是靠不住的。通过我们栏目的这些交流碰撞,知道山外有山,知道别人的坚持,以及知道别人的背后的努力、别人的甘苦,可能对自己的创作也是一种鼓励。
读品:作家不可能是完美的,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毛病是 " 基因 " 里带的,可能很难克服。
贾梦玮:当然了,不仅是不完美的,而且我们这几代作家,我刚才说基础病,有些东西可能是相通的。如果我将来有机会做这种研究,也许会把这些作家综合起来谈他们的基础病——这是我们中国作家,一代、两代、三代,大家可能共有的。
读品:《文学六国论》里的批评是非常尖锐的,现在已经十来年过去了,这些作家一直在不停地创作。您觉得当初提出的那些问题,他们解决了吗?
贾梦玮:我们以后可以把栏目重捡起来,让过去的论者再论这些作家, 十年来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改善,或者有什么倒退。我想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不是做研究的,就我的了解,这些作家基本上还都是在自己原来的局面上在打拼,你说他挣扎也好,你说他挣脱也好,你说他修复自我也好,超越自我也好,他们其实真的都是在做自己的努力。就是贾平凹先生这几年的创作,其实批评家说的那些问题,我想不管他注意到或是没注意到,他一直是在努力,一直是对自己有所超越的。我去年看过他的两个长篇,应该说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非常简单的透明的真诚的那种状态。另外,有些作品可能暂时还出不来。
现代快报 + 记者 白雁 王凡 / 文 牛华新 苏蕊 / 摄
(编辑 张宇)
- 南京
- 2022-06-11 21:34:12
- 南京
- 2022-06-11 21:32:16
- 南京
- 2022-06-11 21:31:42
- 南京
- 2022-06-11 21:30:36